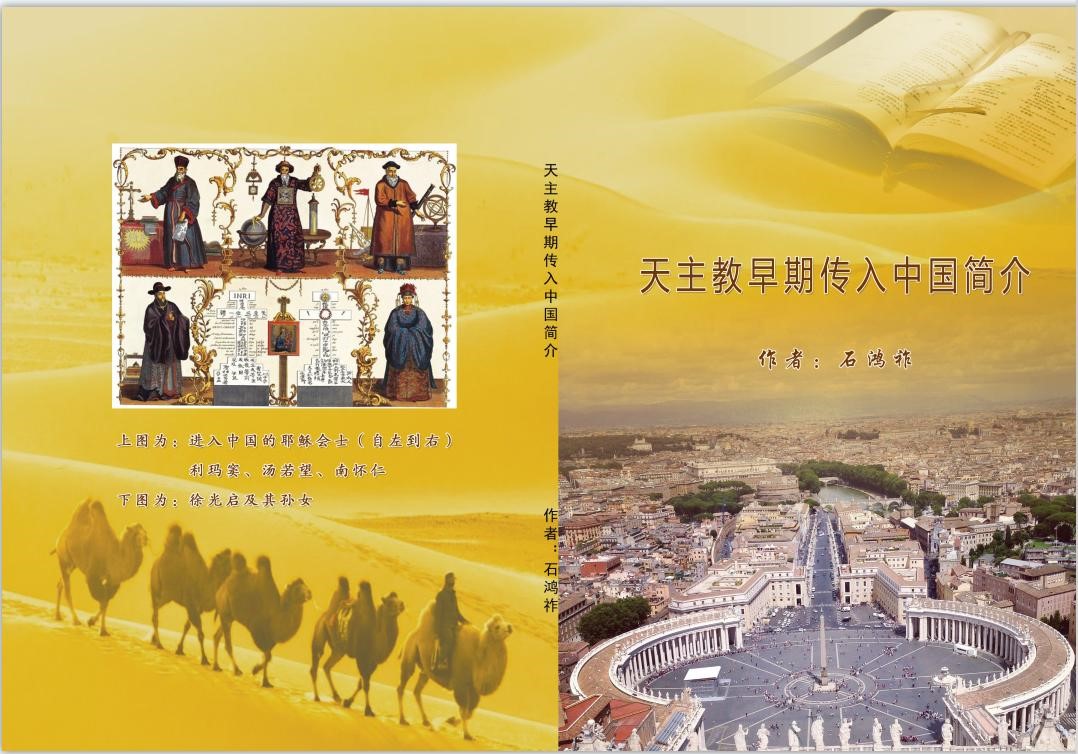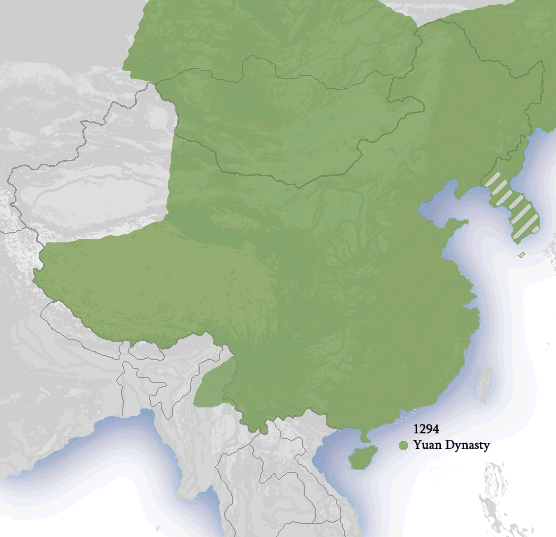雷震远:《内在的敌人》(一)*
第一编 赤祸洪潮渗进
第一章 战火蔓延到安国县──一九三七年

一九三七年九月的一个夜里,周围的情况正和我七年来在华北的其他早秋夜里情形差不 多。
我还是做著同样工作,过著一向习惯的生活,只是我每天的工作在逐渐增加了,因 为自从日本
军队入侵后,逃难的人民一天天地在增多。从七七芦沟桥事变发生后,到现 在是两个半月了,
难民不断地向南逃来,只是我们在安国县城西门外的教堂收容所里, 便收容了三千多名难民。
安国县在北平南一百英里,日本的飞机每天飞来轰炸。来到这里的中国难民,许多都带 了
伤,更有些吓得生病,大都是囊中一文不名。我们只有少量的粮食,只有中国籍的修 士修女,
主教和我自己,但是我们一直维持得很好。
我相信情势会改善,我那时候还是个乐观主义者,因为我才三十二岁,我自己抱有无限 的
信心。在那天夜里,如果我能够预料到日本的侵略恐怖仅是开端,如果我能预料到这 种恐怖会
造成共产党的绝顶野蛮,(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九年间,当我生活在共产党 的统治下并和他
们来往时,我曾一再目睹这种野蛮行动)我那时的信心便会整个动摇。
在这几年内,除去被日本人拘禁的两年半外,我看到共产党的行动没有一项不是为了推 展
共产主义而采取的。那时候有少数人曾看出,共产党和中国国民政府的「联合阵线」 乃是由于莫
斯科的命令。它所宣称的目的是对抗「共同敌人──日本」。从我的经验里 看来,这项宣称的目的
全是次要的,甚至是临时偶然的,他们的真正主要目的,在于渗 透进华中地区,进而在最后攫
取全部土地及政权,并利用人民的爱国热情,以期用阴谋 和武力强使国民接受这种野蛮的思想。
但是在那年九月凉爽的秋分节夜间,我对这些事还都茫然不解。我没有先见之明,我预 想
不到在将来会发生什么情事。我也绝没有想到那天夜里发生的一件小事竟改变了我定 型的生活。
那天经过整日的辛苦工作后,身体备感疲劳,我很早地便上床就寝。这时候是万籁俱静 了。
教堂里面所有的声音都沈寂下去。但那晚又是那样地充满刺激性,使我无法安眠。 所有纷纭的思
想和旧日的回忆都一齐涌上心头。七年前,当我搭船离开欧洲的时候,我 便看到我不仅是抛开
我的旧日生活,并且离弃了我的家庭和朋友,弃绝了我祖先和我青 年时期所生活的西方世界。
在中国,我已经投身于一个新的生活,我虽然是此地教会里 的唯一欧洲人,方圆几十哩内的唯
一外国人,但我一些不感觉孤独和陌生。我好像生来 就是注定渡这种生活和职业的;渐渐地,
我完全熟习东方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了。
那天晚上,我心情扰攘不能安眠的情形,还是极少有的现象;我回想起在比利时的孩提 时
期和第一次大战中在英国的童年时期,旧日的情景都清晰地像一连串图画般地映上心 头。我忽
然想到两星期前──九月十三日──是我的生日,这样一个可纪念的日子竟忽 略过去了。我在
一九零五年降生于科特莱(Vervios)城。我的父亲是一位采矿工程师,在 三十八岁时逝世,丢下
我的母亲和五个孩子。我是最大的孩子。母亲自然便让我做了 「这家里的小家长」。
父亲死后一个月,战争爆发了,母亲带著我们到了伦敦。我和弟弟法兰克在伦敦进小学 读
书。两个妹妹和另一个弟弟由母亲在家庭施以教导。后来有几个比利时耶稣教会教士 在哈斯丁开
设一所学校,我和法兰克便到那里读书。
我们曾看到德国的徐柏林式飞机袭击伦敦,我们害怕得不得了,因为我们是远离祖国的 孩
子,我们晓得家乡已被敌人蹂躏殆尽了。但直到停战后我们在一九一丸年返回比利时 的时候,
才看到房屋毁于炮火,家产全归一烬。外祖母家住在东部边境的小城里,是比 利时与德国交界
的第一个城市,她带著一群孩子们回到那里,我们家庭已经没有什么钱。 但是母亲还把我和法
兰克送到佛维尔(Verviers)的取稣教会学校读书。她时常说:「我们 可以在旁处省钱,但不能牺
牲教育」。
一九二零年,常我才十五岁的时候,我遇到了雷鸣远神父,他刚刚从中国回来,他在中 国
已经住了许多年。那时他正在欧洲协助二千多名由于中法银行倒闭而断绝经济来源的 中国溜学
生。中法银行便是在法国支持共产党组织的银行。在所谓「毛泽东计画」下来 法国留学的中国学生,
不再能从法国的社会主义党及共产党手里获到金钱,虽然法国社 会主义党和共产党曾欢迎甚至
鼓励他们来法国;他们也无法从国内家庭方面获到接济, 因为那时的中国正陷于军阀的混战,
孙中山先生建立民国,刚刚开始九年,从制到民 国的演变正在进行中。那时我年纪还青,对一
切事情的意义还很模糊。共产主义已经用 暴力方式在俄国成功三年了,正在向中国和亚洲伸张;
一位北京大学的学生毛泽东拟订 一个计画,使他的同学们留学法国,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及共产
主义的哲学和方法,而形 成他在日后赤化中国的庞大计画下的核心份子,这项计画竟在三十年
后实现了。(注) 雷鸣远神父照顾著这些留学生,当他看到他们已经陷于政治阴谋的圈套
时,他便设 法尽力拯救他们。他在思想和精神上都是最进步的人,关心中国的进步与改善,关
心中 国人民的物质及精神幸幅。他那种伟大不自私的献身精神,使人人都晓得他是一个「已 经
成为中国人的外国人」了。他晓得这些断绝经济来源的中国学生,大部份都是具有爱 国热忱及正
直思想的青年,他们留学欧洲,是希望在返国后对建设新中国的工作有所贡 献,他开始旅行于
法国,比利时及荷兰,设法对他们加以协助,他越遇到困难时,他越 是使出全副精神加以克服。
当他抵达比利时的时候,我遇到了他。我那时虽然还是个孩子,我立刻看出,如果 我能追随雷
鸣远神父到中国去,在他的手下服务,并以一生精力像他那样地献给中国和 中国人民时,我便
可以真能实现我一生的目的,完成我一向的抱负。
(注) :原著谓毛泽东为北大学生,及拟订留学计画等,均有误。按毛泽东曾任北大图书馆 职
员。
一九三七年九月的那个夜里,当我睡在安国县城的那张小床上的时候,我回想到十七年 前,
首次遇到雷鸣远神父的那个可纪念的日子。我看出他的力量和热情,和他孱弱躯体 里所蕴藏的
不可制服的精神。当我把我的意念向他讲出时,我看出他凝视著我的目光, 流露出一个问题。他
用深刻的眼光向著我注视,好像是在研究这是不是一个孩子的幻想, 抑是我能否具有像我所表
示的那种志愿。
他告诉我静候到毕业以后。他发现出我有些不耐,但是他不曾讲出口。以后他时常来比 利时,
我担任起他的秘书工作,时常谈些问题。我们永远谈到中国。他很少指导我的研 究工作,他鼓励
我继续艰苦的体力工作,其实这乃是我一向习惯的事情。我的体力一直 发育得很好。我的父亲曾
教给我若干种运动。我能够滑雪,游泳,拳击,足球,爬山, 及负重做长程旅行。我作过许多用
膂力的运动,当我到了二十岁的时候,我必须应徵入 伍服国民兵役。我是家庭里的长子,我可
以自己选择我服务的部门。于是我选择了骑兵 ,希望能够训练起骑马术。
在那个辗转不眠的夜间,我微笑著想起我在比利时所骑的英勇骏马,拿它和蒙古马相比,
更和我在华北游山时所骑的小毛驴相比。
雷鸣远神父在欧洲住了七年。在他回中国之前,他已经看到中国的另一伟大希望。一九 二六
年,他曾在罗马参加六位中国主教的任命典礼。一九二七年一月,雷鸣远神父返回 中国,在安
国县的孙麦祺(译音MelohiorSun〕主教下任职,孙主教便是在罗马任命的一 名主教。雷鸣远神
父离开欧洲前,他介绍我去拜访孙主教,孙主教又介绍我到卢芳 (Loavain)神学院读书。在我
服兵役之前,我曾在卢芳读过两年书,但不是主修神学。 现在我成为一个神学院学生了,在卢
芳神学研究所攻读硕士课程。这个研究所是枢机主 教马赐尔主持成立的,美国的佛尔敦主教
(Fulton J.Sheen)便是这里的毕业生,后来我在 中国的时候曾遇到佛主教。
我在那里攻读哲学、神学、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和恩格斯,我开始认识了天主教 的这些敌
人。我在卢芳大学读书的时候,使我学习到酷爱真理,并且同样尊重那些真理 的敌人所使用的
武力。当我研究唯物哲学的时候,我从来没想到我会亲眼看到共产党竟 运用武力和暴力把这些
理论加诸中国人民的身上,促成中国文化的全面改变。
过去的事迹纷纷涌上脑海。我一时沈湎在这些回忆里。随后,现实将我从回忆里唤 出。教堂
里传出一阵犬吠声。我听到了一个生病孩子的低微号泣声,金风的吹袭声,最 后,我沈沈地睡
著了。当我再醒过来的时候,我好像觉得只睡了几分钟。我听到守门人 和另外一个人在谈话,那
时候夜间只有三点,雄鸡还不曾报晓;我从床上起来穿好衣服, 教堂的侍童在房门外敲门了。
和他一齐走进房门的是张仰文(译音)县长的信差。我和张 县长已经有五年多的友谊,我晓得他
在深夜时分派人送信给我一定是有些重大事件发生。 信差的面部没有什么表情。但我却极感不安,
赶快撕开书信,在朦胧的光线下阅读下去。
这封信写得很简略:县长已经奉到率领县府职员及警察撤离安国的命令。他来不及 亲自向
我告别,很觉抱歉,因为他所奉的命令是立即撤离。
我立刻晓得了他何以要选择这样的深夜时间来告诉我这项惊人的消息。他想在国军 到达之
前,委托我协助这县的人民,以便当日军袭击时采取适当的措施。我们曾经作过 若干次的长夜
谈话,就政治经济及哲学问题交换意见。在若干问题上,我们都同意于基 本原则。当我们成篇至
友以后,他时常和我讨论地方问题,他晓得我对这些问题都非常 熟悉。
现在已经是教堂里人们要起身的时候了,我立即走到主教房间、告诉他发生的事件。 他极
关切安国县城的安全。因为他是个中国人,他比我知道得更清楚,一个五万人口的 县城,在没
有警察,没有任何行政当局下是如何的危险,尤其是日本军队离得这样近, 还有大批生人杂在
难民群里继续涌来。
王约翰(JohnWang)虽然是个很优秀的中国主教,但在思想上是中国农民的头脑,他 最先想
到的是那些穷人,下层阶级,难民和无亲无告的人们的危机。
那时他约有五十八岁,中等身材,圆面孔,带著眼镜,额下留著短须,颜色已转灰 白。他
的整个仪表是沈静和霭;这种沈静的外表乃是他在牺牲救世的精神下,内心沈静 与和谧的流露。
我们这些在他手下做事的人,都经过严格的训练;但他总是身先作则从来不请求别 人担任
些比他本人所担任更多的事务。举一个例来说,我们的伙食津贴每人最高仅相当 两块五角美元。
我们只能吃最粗的农人伙食──每天吃小米饭和盐水炒青菜,一星期吃 两次面包,一年四次大
节日才吃肉。
当我刚来到安国县在王主教和另一位中国老教士方神父下面担任职务时,他曾告诉 我他过
份节约的原因。
「我是农人出身,」他说,「如果我不是主教的话,我仍旧是个农夫,每天吃著农 夫的伙食。因此,
我虽然做了主教,我仍愿吃农夫所吃的饭,把节省下的钱用来作民众 教育,而不仅是为了中国
天主教徒」。
我在那时候总觉得肚皮饿,因为我在比利时过惯了不同的生活,但是我觉得羞于抱 怨,又
不好意思要求比那个较我又老又弱的主教或那些非教士的教堂人员多加一些饭他 们都和我一样
地艰苦长时间地操作。
在追随这位主教的清苦节约生活后,我的意志越发坚强,身体越发健壮。在我日后 的生活
中,我对这点锻练更为感激涕零。现在,主教正在凝神思考,我注视著他的面孔, 我自己在想
著:他精神的严肃,使他的表情是如何的感人啊!他沈默了一会。随后他开 始谈到县城牢狱里
囚禁的那些犯人。
主教对他们很担心,我也同样关切他们;因为我在那牢狱里设有一个小型学校,并 且给半
数的囚犯施过洗礼。我们对这些囚犯的如此关切,好像也有些奇怪,但这里却有 许多原因。安国
县城已经拥满难民,城里的人民都不愿意这些罪犯们再分去他们那一点 可怜数量的食粮配给,
也没有人有功夫去保护他们,但是我们又没有释放他们的权力, 于是我们为这件问题大伤脑筋。
我尽速地跑到县政府,看看到底已经发生了什么事。我乘著脚踏车穿进县政府大门, 把脚
踏车停在院里,开始到各处查看。全部警察都走光了,整个县政府里面连一个卫兵 也找不到。县
长办公室的门没有下锁,我顺步走了进去。里面寂无一人。县政府全部都 空了。好的是电话还没
有断。我按著次序往邻近的四个县──蠡县、博野、深泽和安平 ──的县长办公室挂电话、对面电
话铃大响,但房子都空了。显然是这些县的县政府官 员都同时奉命撤离了。
于是我赶快走到牢狱。中国县城的牢狱建筑都是一样的,有三层牢墙,第三层墙的 里面是
牢房。每层墙都装有坚厚的大木门,外面上著铁锁。每个囚犯都带著脚镣,夜间 更把脚镣联锁到
一起,以防止脱逃。
当我看到门上的大铁锁时,我晓得囚犯们还关在里面。我高声喊了一声。他们立刻 辨出我
的声音,在里面答话。我晓得他们还都在里面。我更看出,如果没人照管他们的 话,他们终要饿
死。但是我没有权力释放他们,因为我既非县长,也不是行政当局。如 果我自己把他们释放出狱,
结果他们竟掠劫了这个县城,或纵使任何一名囚徒触犯些轻 微罪行时,全城人士都会一致反对
我。战争已经在各地造成紧张情势,敌人侵入的危机 随时都会发生。
在疑难不决之下,我走去拜访安国商会会长蒲文浦(译音PuWen-Pu)先生。蒲先生 是县城
里的大户,有权势,也有声望。
「你能够帮助我放出那些囚犯吗」?我问他道。
他听到我的话表示非常震骇,他注视著我,好像觉得我在发疯。「什么?把那些囚 犯放出
来?他们会掠劫全城的!他们会杀害并抢劫每个人──而且要强奸妇女呢!我不 愿担起释放罪
犯的责任」他简直地说出。「如果你想那样做时,你去做好了──我允许 你那样做」,他带著
讽刺的口吻讲道。
但是这并不是我想得到的答覆。那根本不能解决这件问题。
因此,我再设法去找另一有权势的人──舒慰农(译音)先生。他也不愿意这样做, 惟恐
有什么危险的后果发生。
如果这两个人都反对释放囚犯时,我真不晓得谁再能支持这项行动了。我失望著向 教堂的
路走回,迎面一个骑著骡子的兵士,沿著大路飞跑过来。我认识他是本城的孩子, 便向他打个
招呼。
「你是那个番号的」?我问他道。 「第三军第二师」,他回答著说。 「你们的师长是
谁」?我又问他。 「唐海源(译音)将军」。他答道。
这真是一个好消息。我和唐将军以前有过来往,我想我可以和他谈一谈。「唐师长 来了
吗?」我问著那位兵士。他转著头来告诉我说,唐将军就要到,但嘱咐我行勤小心。 「唐将军就要
从西门开到」他说。「他和其他官员都是徒步。当兵的骑马或骑骡子」。
在战争初期,日本军队集中目标轰炸射击军官,他们认为军官被射死后,便可以很 容易地
击溃统率无人的军队。但这些机智敏捷的中国军队,很快地看出敌人的轰炸和机 枪扫射都集中
于骑马和骑骡的队伍。那日早晨,我首次看到国军施用巧技诈骗敌人的方 法。
那个兵士扬鞭飞驰而去,我立刻跑到西门等候唐将军。当他到了以后,我个略致寒 喧,我
便请他偕同其他官员到教堂里去用饭。几日来他们没吃到一餐热饭了,他们自然 欢迎我的邀请。
教堂的厨夫飞炔地准备妥一席简单而精致的午餐。我们并且弄到一些酒来招待这些 上宾。
几天来的疲乏下,他们初次得到一会安歇,并且享到这顿午饭,和当地的安谧和 秩序。
在吃饭中间,我渐渐和他谈到囚犯问题,并要求他能否把他们释放出来。他告诉我 他不能
这样做,他是个军人,不能干预县里的地方政务。
但是我并没有绝望。饭后,我把他请到一旁对他讲道:「唐将军,按西方的习惯, 说「不
行」的时候就是「不行」。按中国的习惯,这里还有商量。」
他哈哈大笑起来,觉得这位外国人竟能把中国人的心理实用到一件中国地方问题上, 倒是
一件趣事。他一边笑著问我打算怎样做。我便简直地把我的意思告诉他。
「请你拨给我几名兵士,到牢狱去把那些人放出来。不然他们便会死掉。 「你关心这些囚犯─
─你?」他问我道。 「是的」,我坦白地说。「他们之中的半数经我施过洗礼。我使他们信了天
主教, 我可以相信他们。」
「这种情形你为什么不早说呢」?他问著我,几乎竟是等不及地要帮我的忙了。
他吩咐副官传进几名兵士,我带著他们再奔向牢。我们打开外面两道大门的铁锁, 再打开
最里面牢门的铁锁。当我那天一早到牢狱以后,囚犯们已经猜想到出了毛病。他 们已经没有饭吃
没有水喝,并且也没有卸除下系在一起的脚锁。
在兵士们卸除他们的脚锁之前,我先告诉他们说,我是代表唐将军向他们讲话的。
「在唐将军的恩惠下,你们将获到释放。他并且允许你们自做选择,加入他的军队, 去我
的教堂,或是回家。但是,」我说──这是我自己的意思──「如果你们胆敢抢掠, 或纵使在城
里髑犯极小的罪名时,便立时就地正法。这是师长的命令。」
犯人们喊著他们愿意接受这些条件。兵士们使他们整著队走出三重大门,大部份的人都 愿
意回家,只有少数几个人愿意投军。使我感到有些悲哀的是没有人愿意随我到教堂去, 甚至那
些经过我施洗礼的人也不愿如此。但是这件事情对我一生的影响程度,超过任何 人的想像以上。
这件事只不过是根据人道精神的行动。但由于环境和时间的特殊,人们 都夸张著这件事情的重
要性。城里人民对囚徒们的被释离城都异常欢悦,并且城里也不 曾发生什么事故,于是在第二
天他们便推举了一群代表来到教堂,要求我出任县长。
当地人民对我的信赖,使我异常感动,但是我认为这工作对我是不适宜的,我是这 里的唯
一外国人,一个天主教神父,不适于做一个五十万人口县份的行政长官。
我提出了这几点难题,我告诉他们我的年纪太轻,在这里仅仅住了七年。他们的发 言人把
我的这些反对意见都抛开一旁。我们反覆地把这件问题讨论了极长的时间。我必 须确实看出这并
不是中国人的客气表示。我必须确实晓得我有担当这种工作的充份能力。 并且我必须认为这是我
应该做的事情。最后,主教替我做了决定,我也觉得满意,因为 这是一个中国人为了中国人的
利益而做的决定,我愿意从中协肋。 整个下午,主教 都在静听我们的讨论。最后他对我说,
「人民需要你。他们希望你所做的事乃是为了人 民的幸福。请你接受这个职位,但不必接受这个
职衔」。
九月二十四日下午我成为河北省安国县代理县长。安国县有五十万人口,其中有五 万人住
在县城里面。
第二天,在我的领导下我们组织起一个行政委员会,命名为临时委员会,仍为代理 性质而
不具实权。我立即开始募集警察,并在全县办理联庄自卫。一个月间,我致力于 各项县政工作。
到了十月二十一日,全县四百多村都完全组织起未,成为几个大联庄, 从事自卫;县城里的警
察也装备妥当;全县各地的政府分设机构也都告成立。
当我们刚完成各种组织后,中国共产党军队便开到了。虽然我们想著他们会来,但 我们毫
无怀疑地都晓得他们的到达会给中国和世界带来怎样的悲剧。共产党的占领,比 中国人所受
到的日本人的屠杀和掠劫还更为残酷可怕,不过人民还没有机会来领略它 的滋味。有些人很快
地便看出共产党的真面目,他们晓得已经堕入陷阱,但已经无法拔 脱了。
当中国国军向前转移后,共产党便从延安基地向东推展,越过重山,转而北上。当 日本军
队侵入中国,军事行动日趋剧烈时,这一场从九一八起中日间不宣而战的战争, 便成为日本企
图征服中国的全面战争。
日本军队沿交通线前进,他们兵力不多,无法占领中国全部。共产党老早就晓得这 种情形,
并晓得如何利用这机会来扩展势力。他们立即占领了日本人所不能占领的地区。 并遵照莫斯科的
命令,把占领地区按严格的共产制度组织起来,毁灭了一切新旧制度, 欺骗老百姓,利用人民
的爱国思想,和幼稚的理想主表,施行恐怖统治,并毁灭所有文 明国家中反抗共产主义的成份。
在中国,反抗共产主义野蛮行动最坚强的份子,是六种宗教。佛教,儒教,道教, 回教,
基督新教和天主教;以及家庭;宗族;秘密会社,中国人的道德传统制度,和中国国民政府。
在这里我必须先说明,俄国共产主义和任何其他共产主义在实际上都是一丘之貉, 不管这
个共产国家所标榜的精神如何。所有共产统治都根据莫斯科征服世界的计画。所 有共产及卫星国
家,都遵守著这项计画。不同之点只是表面上的差异,一般是方法上的 不同。方法上的不同,只
为了临时适应当地的情况,等一切情况改变后,折衷方法便会 停止。折衷方法便是共产党的咒
语。当目的实现后,他们便立刻把它迅速无情地予以根 除。他们也绝不许旁人──共产党除外─
─利用折衷术。妥协的人一旦被共产党发觉后 便不会活得太久。
不久我们便看见这一切丑事在我们面前展露出来,正像是一个魔鬼所绘的一幅中国画。(未完待续)
* 此文所阐述的所有观点仅为此书作者本人(雷震远神父)的观点,不能代表本网站的观点。